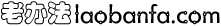阳光的名言
91.树木悲哀吗?树木纵然有悲哀,也不是为人所了解的。树木从发芽到长大,老去枯死,都是在一个地方,除非有人将它移植,否则树木自始自终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生长。而人就不同了,人可以到处乱跑,可以任意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玩自己喜欢玩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固然有人总是在做自己所不愿做的事,吃自己所不喜欢吃的东西,但最起码他还能动,还能走。树木呢?它不喜欢这里的阳光,就可以自己躲起来吗?它不喜欢这里的土质,就可以自己找块好一点的土地吗?不能。所以从人方面来说,树木是悲哀的,是值得同情的。武侠小说家 古龙 《怒剑狂花》
92.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台湾女作家 龙应台
93.我是生死,你是轮回;我是红尘,你是虚空;我是用来标识岁月的某个微不足道的点,你是容纳所有沧海一粟的无垠;我是业障,你是修行;我是渴望成为神的人,你是无法褪尽人气的神;我是“此时此刻”的囚徒,你是“永恒”这片原野上的牧羊人;我是不可能挣脱“此情此景”的肉身,你是天地悠悠的一部分;我是至情至性的欢笑和哭喊,你是高山顶上寂然的雪线;我是照耀微小灰尘的一线阳光,你是拥抱万物的黑暗;我原谅所有琐碎的恶意,你负责评判一切不自知的邪念;我是绚烂缤纷的幻想,你是不情愿地照亮万里海面的灯塔;我觉得我的一生太短,你觉得你的自由太漫长;我是你的南柯一梦,你是我必然到达的终点。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你生我,我生你,我们合二为一,就是宇宙,就是永恒。原名李笛安,中国青春文学女作家 笛安 《宇宙》
94.我其实也诚实地在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台湾女作家 龙应台
95.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您信佛吗?”我问。“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96.那些末日已经临近的,很容易地就能从它们的外表的病态上分辨出来。在它们的背上,是有尘土沾附着的。在它们尚健壮,还年青的时候,它们一旦发现有尘土附着在身上,就会不停地拂拭,把它们黑色、黄色的外衣清洁得十分光亮。然而,当它们有病时,也就无心注意卫生清洁了。因为已经无暇顾及了。它们或是停留在阳光底下,一动也不动,或者很迟缓地踱来踱去。它们已经不再拂拭它们的衣裳了,因为这已不再重要了,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这种对装束的不在意,就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过了两三天以后,这个身上带有尘土的动物,便最后一次离开它自己的巢穴。它跑出来,主要是打算再最后享受一点日光的温暖。忽然,它跌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再也不能够重新爬起来了。它尽量避免自己死在它所热爱和生存的巢里。这是因为,在黄蜂中,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规定,那就是巢里是要绝对保持干净整洁的。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黄蜂,要自行解决它自己的葬礼。它把自已跌落在土穴下面的坑里。由于要保持清洁卫生,这些苦行主义者,不愿意自己死在蜂房里。至于那些剩余下来的,还没有死去的黄蜂,它们仍然要保留这种习惯,直到它们最终的结局为止。这形成了一种不曾被摒弃的法律条文。无论黄蜂世界中的人口如何增加,或是减少,这一传统总是要保持遵守的。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文学家 法布尔 《昆虫记》
97.这年的冬天,主人受供销社主任庞虎腿上新装义肢的启发,决心要为我制作一个义蹄。凭借着几年前那段友谊,主人和女主人找到庞虎的妻子王乐云,说明了心情,在王乐云的帮助下,主人和女主人把庞虎的义肢里里外外研究个透彻。庞虎的义肢是到上海一家专为革命残疾军人服务的工厂订做的,我一头驴,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即使是那家工厂愿意为一头毛驴制作假蹄子,我的主人也承担不了昂贵的造价。于是,主人和女主人决定自己动手为我制作一只假蹄子。他们费了整整三个月工夫,做了毁,毁了再做,最后,做出了一只从外观上足可乱真的假蹄子,绑在了我的断肢上。他们拉着我在院子里走了几圈,感觉比绑一只破皮鞋好很多。我的步伐虽然僵硬,但瘸的程度大大减轻。主人牵着我,走在大街上,昂头挺胸,洋洋得意,仿佛示威。我也尽量地往好里走,努力为我的主人长脸。屯里的孩子跟在我们身后看热闹。我看到了路边那些人的目光,听到了他们的议论。他们对我的主人很是佩服。我们与面黄肌瘦的洪泰岳迎面相逢。洪泰岳冷笑着说: “蓝脸,你这是向人民公社示威吗?” “不敢,”我的主人说,“我跟人民公社是井水不犯河水。” “可你走在人民公社的大街上。”洪泰岳低手指指地,抬手指指天,冷冷地说,“可你还呼吸着人民公社的空气,还照着人民公社的阳光。”“没有人民公社之前,这条大街就有,没有人民公社之前,就有空气和阳光。”我的主人说,“这些,是老天爷送给每个人、每个动物的,你们人民公社无权独占!”我的主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街上跺跺脚,仰脸被太阳晒着,说,“好空气,好阳光,真好!”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黑,你大口喘气,死劲踏地,让阳光照着。”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生死疲劳》
98.手风琴的声音像花一样在没有阳光也没有歌颂的黑暗中旁若无人地芬芳着。来自东欧的民间音乐,歌颂着表情阴郁的受苦人们的乡愁。卖艺的老人在地铁站的角落里旁若无人地弹奏,他抬起眼睛,看见了我,对我笑了一下。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听见的音乐是怎样抚慰了我,那个当时十八岁的,穿着一件样式很傻的黑色外套的小姑娘。你知道她那个时候一无所有,除了满脑子的,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不忍心嘲笑的奢望。这个地铁站就像她当时的人生,只有一片黑暗中的疾速,只能在心里惴惴不安地等待下一个有灯光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她看得见站名,她就可以知道她到达了什么地方。她当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她才有在这片黑暗里面往前飞的勇气。不过没有人鼓励她,没有人对她笑,没有人告诉她下一站是哪里,惟一的温暖,就是这个跟她一样的流浪者的音乐。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地铁音乐人。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音乐在巴黎的地下栖居。古典,民谣,爵士……很多人惊讶他们的水准怎么那么高。这些游客们不知道,在巴黎,取得在地铁里卖艺的资格也是要通过考试的。每半年,地铁的管辖机构从一千名左右的候选人中间选出三百五十人,给他们地铁音乐人的许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学院,他们中有很多自己也是流浪的人,他们美丽的音乐,还有他们的潦倒跟落寞,同时被用来建造这个以浪漫闻名的城市的价格不菲的浪漫。巴黎这个地方就是如此,风情万种,但是心冷似铁。如果你说这整个城市是一场令人眩目的盛宴,那这些地铁音乐人就是盛宴散场时的落寞残羹。他们其实也是美丽的,他们其实也是嚣张的,只不过,已无人关心。 地铁站怕是城市里最容易激起人乡愁的地方。于是他们选择了在那里生存。 他们旁若无人地演奏,哪怕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地铁开过来时,那撕裂了空气的尖锐的呼啸声遮掩了一切人间的声音,但是他们无动于衷。人们上车,下车,地铁重新开走,站台上暂时寂静。他们的音乐就往往在这个时候,像海水退潮时候的礁石那样浮了上来,带着刚刚冲刷过的潮气。 五年以后的今天,我把他们,这些地铁音乐人当成了我论文的题目。我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解释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没有什么人关心,因此也就没有多少资料可以查询的群体。我没有办法对一群陌生人说,在内心深处,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跟他们一样,都是这分外妖娆又无情无义的江湖上的卖艺人。你可以轻视我,可以瞧不起我,可以把我当成是被这个寻常世界排斥在外的人,但是客官,我请问你,若是没有我的音乐,你真的确定你自己可以像从前那样活下去?所有的盛宴惟一的结局就是散场,所有的繁华惟一的终点就是凋零。你看不到这点,但我可以。因为我所有的美丽,原本就绽放于衰败之中。你的残羹就是我的夜宴,你的消遣就是我的尊严,当你不屑地把一枚硬币丢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忘了,我比你更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原名李笛安,中国青春文学女作家 笛安